读书 | 《最好的告别》:在生命的褶皱中寻找尊严与自由
《最好的告别》:在生命的褶皱中寻找尊严与自由
高考倒计时的某天深夜,我正用红笔修改第不知道多少张理综试卷时,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我打开手机,惊喜于屏幕中许久未见的表叔,下一秒镜头调转,我脸上的笑容却霎时凝固,重症监护室走廊被刷的惨白的墙面上,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在玻璃窗后晃动,屏幕的中央,爷爷蜷缩在中央,浑身插满导管,宛如一株被钢筋固定的老树——这是我对"医疗化生存"最初的认知。
阿图·葛文德在《最好的告别》中描述的"技术迷恋"正在这个无菌空间上演。我们签署的每张抢救同意书都像一份荒诞的考卷:血滤机置换量填3000ml,升压药剂量精确到0.1μg/kg/min。主治医师用CT片在灯箱上勾画着多器官衰竭的版图,那些黑色的阴影像极了高考错题本上的红叉。之后的故事就像书中大多数人的经历,预后不良,之后选择送回家进行最后的告别。
那晚汽车载着拔掉鼻饲管的爷爷驶离医院时,我只觉得那是一种安静,逃离了滴滴作响的仪器,逃离了悉悉索索的笔触,如今读完这本书,我忽然想起书中那位选择放弃化疗的老教授。监护仪撤走后的车厢里,老人喉咙发出风穿过枯枝的声响,"生命自主权"——那些被小数点后的医疗参数挤压的生存实感,此刻正在溃散的呼吸中缓慢复苏。

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——泰戈尔的诗句被反复引用,却鲜有人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哲学重量。书中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:无论医学如何进步,衰老与死亡始终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。要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放手,ICU是生命被治疗的最后场所,却不应成为生命最后终止的场所,将ICU视为“生死战场”,实则是将技术理性内化为信仰体系。当医学从“对抗疾病”异化为“对抗死亡”,救赎便沦为西西弗斯式的永恒苦役。
作者通过父亲罹患癌症的案例,展现了生命的脆弱:即便身为医生,面对疾病时也如普通人般无助,最终选择放弃过度治疗,以姑息医疗换取最后的安宁时光。这种选择并非消极妥协,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——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度,而在于质量的厚度。
书中提到,人活着需要“一个超出自身的理由”,无论是家庭、爱好还是责任。这种追求在衰老时尤为凸显:当身体逐渐失控,唯有精神的自主性才能抵御虚无。正如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在疗养院中通过照料植物重获价值感,生命的尊严往往藏匿于看似微小的选择权中。而这恰引出了我对这本书的第二个思考,即医生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应是什么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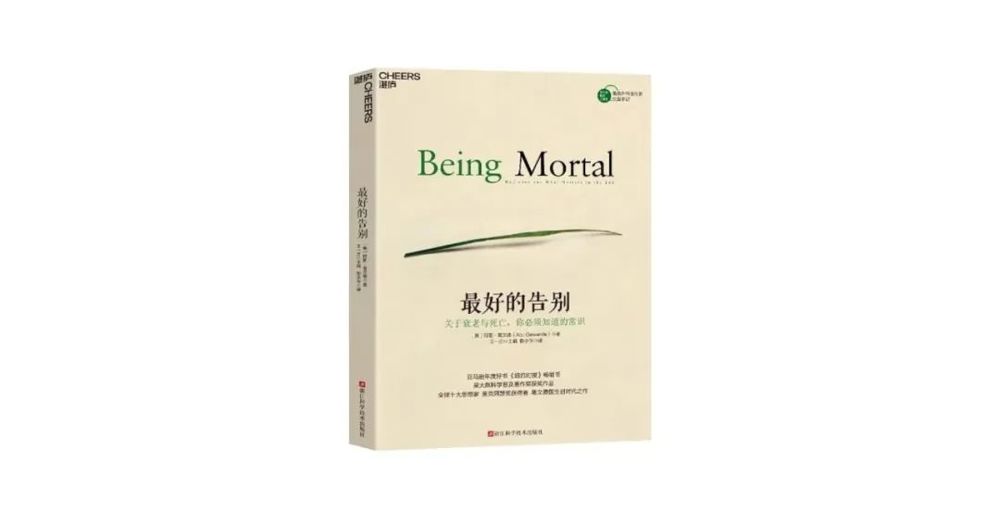
书中提到了三种医患关系,即家长型、咨询型和解释型,书中批判了“家长型”医患关系——医生以权威姿态决定治疗方案,而病人沦为被动的接受者。与之对比,“解释型”医患关系强调共同决策,医生需倾听患者的生命诉求,而非仅关注病理指标。我们总是学习一个又一个的案例,但可能并未意识到每个例子之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,只有我们先把每个病人都当成人来看待,我们做出的一切努力才是有意义的。毕竟最好的医疗决策不是技术最优解,而是与患者人生故事深度契合的选择。
最后的几天里,爷爷就躺在他曾一直睡觉的床上,呼吸逐渐变得平缓,陪着他的那段时间里,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的状态,偶尔睁开眼,我都不确定他是否意识还清醒,只是看着他浑浊而暗淡的双眸微微颤抖,却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。呼吸机的存在使他根本无法开口讲话,我们都知道,一旦拔开呼吸机,他将很快的离开我们,但是,家人都没有去拔,直到某天预定好的良辰吉时,表叔才选择让他离开我们。我一直在深思,这样为良辰吉时而一直让祖父受苦是真的对他好么。传统与现代对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。现代社会通过临终关怀与“预先医疗指示”赋予个体选择权;而传统文化中,“死亡”是讳莫如深的禁忌,子女常以“孝”之名过度干预父母的生命选择。而这往往会适得其反,恰是“以爱为名”的绑架——忽视老人对熟悉环境的心理依赖。真正的孝顺,应是尊重其意愿,而非强加自以为是的“最佳方案”。

阿图·葛文德医生 (from PBS)
不久后,我成为了一名医学生,开始正式系统全面了了解人类的生老病死,我也比以往都更加执着于去了解如何面对死亡,《最好的告别》最终指向一个终极答案:即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。答案藏匿于作者父亲的临终选择——放弃无意义的抢救,转而竞选社区总监、完成巡回演讲,在家人陪伴下书写最后的生命篇章。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勇气,是对现代医学过度干预的抵抗,更是对人性尊严的终极捍卫。生命的褶皱中,衰老与死亡并非黯淡的终点,而是照亮存在意义的星光。当我们学会与必然的失去和解,才能真正拥抱每一刻的鲜活。正如书中所言: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,遗忘才是。”而最好的告别,是在记忆尚未褪色时,让爱与尊严永驻。
作者:高彰岳
深圳大学2023级临床医学专业
(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,公有版权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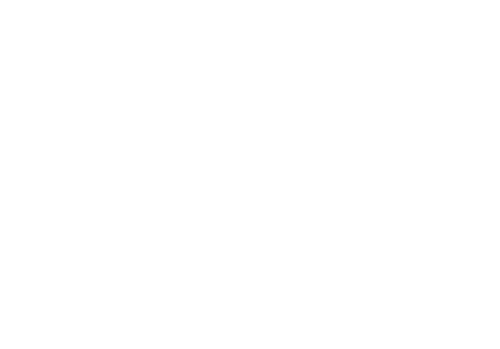
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