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行病历 | 听见
听见
作者:刘雨暄
深圳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2023级
这世上总有生命从枯枝飘落,零落一地,你听见的,是脚踩过的沙沙作响;也总有生命破土而出,汲取养分,你难以听见的,是血肉生长的声音。
此次温暖的医学实践主题是“生”,我们要采访的对象是27岁的杜姐姐。一走进产房,就见她半卧靠在病床上,两只手从被子里伸出,轻轻搭在腿上,脸色有些苍白。我们围坐在杜姐姐身边,攀谈起来。
“姐姐这次怀孕是有准备的吗?”组长率先开口。
杜姐姐稍微抬了抬头,回忆着:“是的,我跟我老公备孕了三个月左右。”
“那姐姐怀孕的时候有什么孕反应吗?”
“我还好啦。”杜姐姐笑了笑,语气轻快,“孕反应什么的都不严重,到后面几个星期才会有胎动。我之前有一次开会,他一直踢我,我的腰特别痒,但是当时又在开会也不能挠。”一提起孩子,杜姐姐的脸色突然红润起来,手在身体两侧一搭,脸上荡漾着笑容。她的幸福感染了我们,大家都咯咯笑了起来。
谈起怀孕的过程,杜姐姐说从备孕到产检孕前都比较顺利。“不过,生的时候痛死我了。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,其实我刚刚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冒冷汗。”我抬头仔细一看,果然,杜姐姐的额头上泛着一层薄薄的冷汗。 杜姐姐又补充道,“我打了镇痛,还以为会立刻不痛了,结果是慢慢不痛,不过后面把头生出来就好了。”
“那姐姐在生产结束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呢?”我问到。
“就和排便一样。”我们都被杜姐姐的形容惊得睁大了眼睛,却见杜姐姐笑着对我们点头,“对,在肚子里的家伙终于落地了,长吁了一口气的感觉。”大家面面相觑,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。
杜姐姐幽默的回答,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本以为她会说生产结束后的第一感受是激动、幸福,或是对新生命的欣喜与爱,却没想到会是这样“玩笑”般的形容。可转念一想,这真的是玩笑吗?

面对生产这件大事,我们总是歌颂母亲的伟大,母爱的无私,理所应当地认为讨论到小孩出生的那一刻,应当是母亲对孩子爱的表达。
可是,生产从来就不是那一刻,而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。
从备孕到孩子出生,这十个月的漫长时间里,杜姐姐一定无数次幻想过第一次见到宝宝的场景。她可能想象过宝宝的模样、第一次触碰时的柔软,甚至在心里勾勒过未来生活的美好画面。然而,当她真正躺在产房的病床上时,面对分娩的剧痛,身体仿佛被撕裂得支离破碎,灵魂随时会飞散,她却依然咬紧牙关,在痛楚与疲惫中坚持着,直到宝宝的头终于露出。
结束“战斗”的这一刻,情感的潮水涌来,激动、幸福、甚至难以置信的欣喜都在心头交织,但最真实的反应,却是如释重负般的深深松了一口气——那种从极限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轻松,是她身体与灵魂所经历的一场艰难胜利的真切感受。在这一刻,生命延续的奇迹与母亲付出的伟大交织,化作了最真实的体验。
后面我们又和杜姐姐聊了些产后的安排,提到坐月子时吃些补品,杜姐姐却说不能吃太补,不然发胖之后就瘦不下来了。她之前都没有减过肥,因为根本坚持不下来,这次怀孕过后她也不知道肉长在哪里了,但就一直感觉自己胖了。
不仅是产后恢复,育儿问题她也不由得感到焦虑,“现在小孩太卷了,各种辅导班。而且生了小孩之后花销也很大,你们背后那么一小罐奶粉就要几百块钱。一个月两千块奶粉,还要买纸尿裤。”关于以后带小孩的事,杜姐姐更是满脸发愁,“只有一个人上班赚钱肯定也是不行的,现在深圳这边很多都是父母帮忙带小孩,哎,以后再说吧。”提到二胎,杜姐姐也是直言没有这个打算,尤其在生了一个小孩之后。
从和杜姐姐的对话中,比起幸福,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初为人母的茫然、育儿的压力以及产后康复的焦虑。
“我一路向前,却无法到达目的地;仿佛我登上一列火车,从车窗能看到我之前一直走的那条路;火车与那条路平行行驶一段时间后加速,然后匀速地东开一段,又西开一段,开向满是陌生山丘的地方,将一切抛在脑后,任其消失在视野中。”
这是英国女作家蕾切尔·卡斯克在《成为母亲: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》中的独白。“成为母亲”这一刻,她的情绪同样是复杂的——困惑,迷茫,甚至恐惧。她感到自己正在逐渐偏离正确的人生航向,而过往的所有生命经验好像都没办法用在为人母的这个角色上。
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的调查数据显示,全国适龄人口的初婚年龄正在不断推迟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上升至2020年的26.3岁,初育年龄也随之推迟至27.2岁。更引人关注的是,2020年女性终身无孩率接近10%,而2015年仅为6.1%。
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不生育,并坦然道出自己的理由——产后妇科病的困扰、身材走形的焦虑、工作发展的受限、产后抑郁的折磨,以及育儿过程中沉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......这些真实的声音,使人们开始直面母亲这一身份背后的辛酸与不易。
无所不能的人类,以极其脆弱的姿态降生于世,在生命的初期,吃、喝、拉、撒,没有一件事能够独立完成,只能依靠他人。而这个人,大多数情况下是“母亲”。这一天,是一个湿热的、触及心灵的婴儿的诞生,也是一个新的母亲的诞生。从此,除了女儿、妻子等身份以外,她又拥有了“母亲”的身份。
产房外,人人都能听见婴儿响亮的啼哭,便知道这是“生”。可在产房内,又有谁能听见一个孕妇分娩时的哭泣与呐喊、一位新手母亲的艰辛与不易?
母亲常被视为无私奉献的象征,却往往缺乏应有的社会权利。她们在孕育生命时面对的风险与生产时展现的勇气,理应得到更多关注。我们需要听见更多来自母亲的声音,推动职场中母亲与父亲享有平等的地位与待遇,共同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,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平衡与和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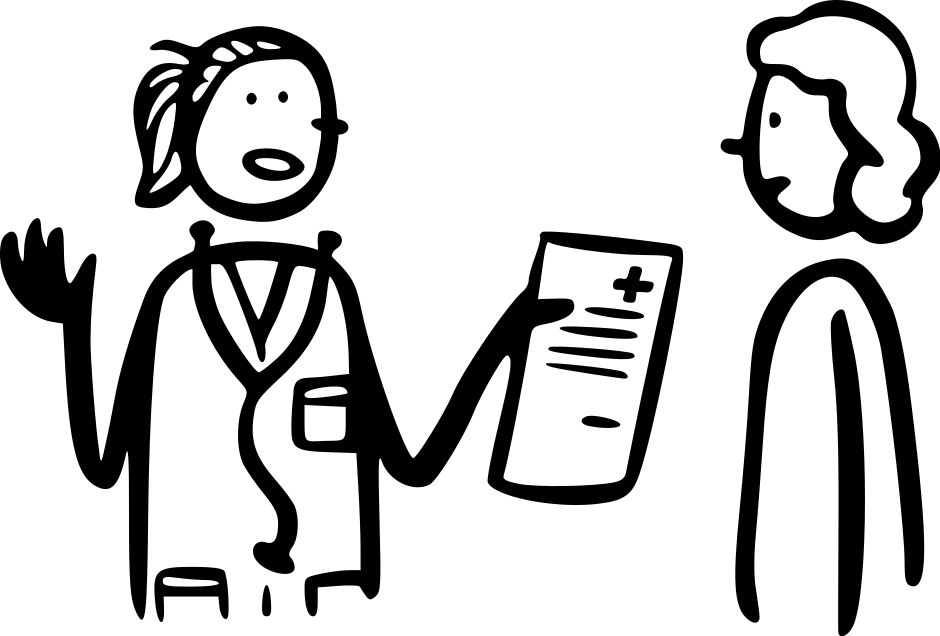
而从医学的角度,我们不应当只重视生产这个过程,产前产后同样重要。孕期呕吐、水肿、腰疼,妊娠纹、漏尿、产后抑郁等等这些问题,都是孕妈妈们切身的痛苦,尤其是漏尿这类问题,不仅苦于疾病本身,更苦于尊严。这些看似普通且普遍的问题,往往被忽视,却深刻影响着母亲们的生活质量。
“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。”
面对这些痛苦,如何解决、如何让母亲们在产前产后更有尊严、如何帮助她们更快地回到从前的状态,都是我们医学生以及医务工作者们需要深思的问题。
鲁迅先生曾说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作为医学生,我们不应妄自菲薄,自以为自身力量过于渺小,而应相信这份责任感是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,只要它在我们的心底生根发芽,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。而到那时,我们的阅历将更加丰富、视野更加开阔、学识更加完备,我们所能做的不仅是治疗与治愈,更是缝补破碎的心灵,听见血肉生长的声音,赋予医学更深远的意义。
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