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行病历 | 迎接人生的尽头
迎接人生的尽头
作者:郭雅贤
深圳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2023级
指导老师:杨迪
深圳大学总医院肿瘤科
一直以来,国人都缺少三种教育:死亡教育、性教育、爱的教育。今天,我接受的正是其中的死亡教育。
No.1面对病魔的态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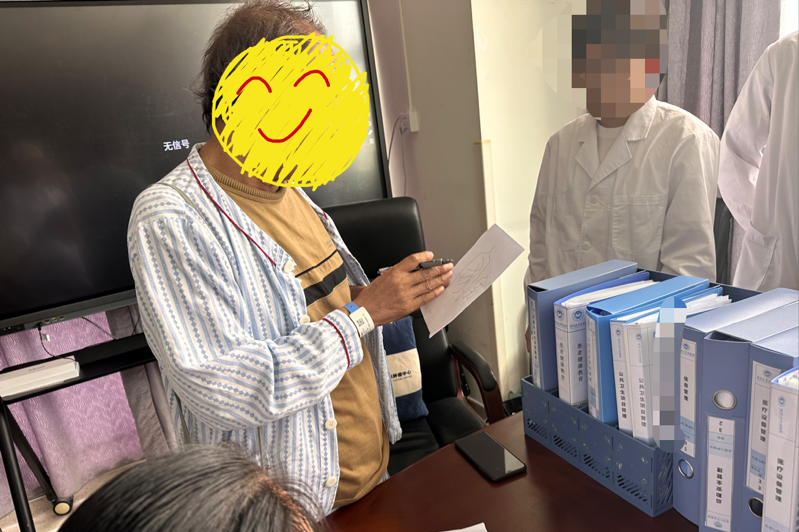
在收到《温暖的医学》课程实践的任务后,我们精心准备了不少访谈的问题和内容,但是真正如何面对一个身患癌症的患者,我们心里都没底。他会不会很看起来很憔悴?他会不会很容易累?他会不会非常悲观?我们的问题会不会是他不想回答的问题?但是在杨迪老师的介绍下,我们对深大总医院的肿瘤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也对今天要访谈的特殊患者有了初步的了解。听闻这是一位清华建筑系毕业的老师,我们的心情又从担心变成了期待。
杨老师带我去病房邀请他时,正看到他笑呵呵地与隔壁床的大叔开着玩笑,调侃做个核磁“震懵了”。他轻松地挎上自己的注射仪器,就像跨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公文包一样,拿起纸笔就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,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。略显红润的脸颊,扬起的嘴角,闪着光芒的双眸,看上去可以说是容光焕发的他,甚至让我们一度忘记了他是身患绝症的人。如果不是他身上的病号服,你真的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已经与胰腺癌抗争了两年的72岁老人。
面对病魔,他没有沉浸在痛苦中,而选择与疾病对话,仿佛与一个老友聊天。他跟胰腺癌说:“哥们,今天感觉还好吗?”还有“你好好的,别折腾我,我多活几年,你不也多活几年吗?你要真整死我了,那多不划算呐。”
他的生活态度,就像他曾经填的一首词《忆秦娥》中所表达的那样:
伴癌乐 北风寒 京都厢道弱身单
弱身单 高楼暗绕 曲巷明还
身染重病虽履慢 笑谈小癌畏吾谦
畏吾谦 心态如神 境界似仙
这是施老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时,身体不适,散步时填的一首词。他用“小癌”来形容自己的绝症,这是一种多么超然的态度。
No.2施老的多重身份与辉煌经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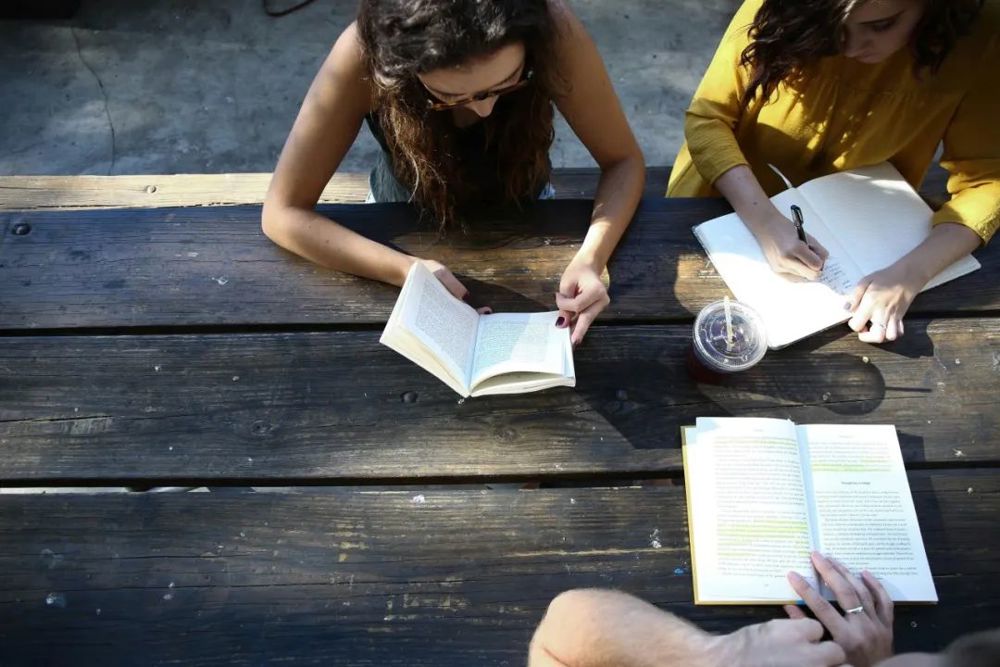
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实践活动。这位患者,我觉得叫他施老,施教授或者施总更合适,叫病号不合适,虽然他也这样开自己的玩笑。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,我们了解了施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先是学历,从东北的农村,走到省城通信专业的中专,再走到首都的清华建筑系。清华,那是多少人的梦想,也是我曾经的梦中学府啊。
今天的实践活动说起来是我们作为医学生对癌症患者的关怀,但是有幸遇见施老这样一位老教授,他告诉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知识。我们大学生要多问,抓住老师解决自己的疑问,学知识要大声读出来,每天都解决一些问题,积累自己的知识和本领,并且要抓住机会展示自己的知识,不仅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,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能力,还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欠缺的地方。针对我平时很懒这一缺点,施老说,懒就是因为没有目标,没有压力。“如果今天不干活儿明天就没饭吃,你今天肯定不懒。”他的话听起来都是简单熟悉的道理,但是真正能坚持做到的一定不是简单的人。我真的不想让宝贵的大学时光荒废过去,施老的话让我受益匪浅,多问问题,敢于展示,坚持目标就是我今后的行动指南。
我们面前的他是一个病号,但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,一位艺术家,一位书法家,一位老师,更是深圳特区建设的参与者。
他是第一批到参与到深圳特区规划建设的建筑师,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国大使馆也出自他之手,项目中标率接近百分之百。说到兴起处,他拿出手机给我们展示自己的作品,站起来为我们分享自己的感悟。种种经历印证着他这辉煌的一生。这位老人不仅实现了自己幼时做建筑师的梦想,还真的做到了为祖国奋斗五十年。

我有些好奇地问:“您还没退休吗?”他却轻松地回答:“退休是看个人意愿的,我还不想退休呢。”是啊,他的一身知识与本领应该属于中国的建设,而不是被病魔夺走。
No.3访谈后的沉浸与思考
两年前,他的女儿曾经满脸泪水地告诉他,医生说他活不过五个月了。施老却乐观地回应:“那不还有一百多天吗?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哈哈哈!” 听到这里,我禁不住心头一热,别人可能都觉得生命只剩五个月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,而他却把这件事说起来那么轻松,好像五个月的时间也是很久的。我怎么做到像施老一样如此坦然地迎接人生的尽头呢?
作为一名未来的医生,我会思考,我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带领病人走出病痛的折磨。作为一名医学生,我在自问,我是否能够不断学习,提升自己,把握好自己眼前的机会。如果作为一名患者,我是否能够像施教授那样,保持如此积极乐观的心态。
前两种身份我都有机会切身体会到,我尝试着“体验”第三种身份,想象如果自己是晚期癌症患者,面对自己的病情,面对亲人,面对朋友,走在生命的尽头,我会有何反应?
事实上,一旦共情,我泪流不止。一般来说,医院告知患者癌症后,他们通常会经历否认期、愤怒期、妥协期、抑郁期、接收期。这些阶段,每一个都充满了挑战,每一个都需要勇气和智慧去面对。我想,在这种生命的特殊时刻,或许我难以做到施老那般的坦然和从容。
在结束上午的访谈后,我依旧久久沉浸在对死亡的思考中。

有人说,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,而是走出了时间。
一个人去世了,好像太阳或者月亮落山了。“但是太阳,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。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,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。”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这么说。
人生有限大,而生命无穷。死亡不是生命的尽头,因为有爱和回忆,因为可以把想念放在心中,生死之间并非不可逾越,生死两相安。
接受死亡不在教科书的,却在每个人考纲之内。如果你也不知道怎么备考,不妨去看一场日出,不妨去种下一棵树,不妨去给死去的亲人写一封信。看日出,去世的人就像月亮,而活着的人是太阳,“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”;种棵树,一个生命,像小树一样长高、长壮实,开花,结果,也会有一个生命像一棵老树一样,慢慢地枯萎、倒下,“落花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这是生命传承的爱;写封信,写信的时候不要把他当做死去,要像活着一样,给远方的亲人讲讲自己的生活、感受体验,因为你在替他体验现在的世界啊。

然而,即使在今天以后,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学会如何面对死亡,如何面对身边亲人朋友的死亡,尤其是这种由癌症带来的死亡。后来,我想明白一句话,人对死亡的害怕,因为对死亡的未知,还因为他们还没好好活过。施老面对癌症的从容或许就是因为他这一生已经足够精彩,他的生命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结束,学生们对他的思念,他传授给别人的知识,他的建筑作品,都会代替他继续“留在这个世界上”。
为了更坦然从容地迎接生命尽头,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,趁还有时间,好好地过好每一天,认真地做事,认真地爱身边的人,认真地不断拓宽人生的宽度,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因为去世而真的结束。我想只有像施老一样真正好好活过之后,我们才能坦然地迎接人生的尽头吧。

用户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